我站在新华书店的收银台后,看着晨光透过玻璃门斜斜地洒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封面上。托尔斯泰笔下那个穿着黑色天鹅绒长裙的女人仿佛正从书脊处向我投来一瞥。这是我在书店工作的第六个年头,前三年都是在门店与书为伴,每天清晨整理书架时,总会有这样的时刻,某本书突然从整齐排列的队伍中跳脱出来,向我诉说它的故事。而我的故事,也正是从这样的相遇开始的。
童年时代,我家住在老街上,隔壁就是一家小小的新华书店。那时的书店不像现在这样灯火通明,木质书架上的油漆已经斑驳,却散发着一种令人安心的松香味。我常常蹲在书架间的过道里,用手指轻轻划过那些书脊。记得第一次被一本书“选中”,是十岁那年的雨季。雨水敲打着书店的铁皮屋檐,我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本《城南旧事》,封面上落着薄薄的灰尘。当我翻开泛黄的书页,林海音笔下的北平胡同就这样毫无预兆地闯入了江南小镇孩子的世界。那些文字像雨水渗入泥土般渗进我的记忆,从此,书店成了我的避风港。
大学毕业后,我毅然决然地来到新华书店上班,这个决定让许多人困惑,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想成为那个为别人递上“钥匙”的人。刚开始工作时,我像整理自家书架那样对待书店里的每一本书,直到门市主任告诉我:“书店不是图书馆,我们要让书与人相遇,而不是单纯地陈列。”他教我观察读者的眼神:当他们的手指在某本书上徘徊不去,当他们的目光在书架间游移不定,那就是需要我出现的时候。
在书店工作的第三年,我遇到了一个总在心理学书架前徘徊的高中生。她纤细的手指不断抚过《自卑与超越》的书脊却从不取下。某个午后,我装作不经意地将一本《被讨厌的勇气》放在她常站的角落。一周后,她红着眼睛来问我还有没有类似的书。那一刻,我明白了老店长的话——书的价值不在于被完美地陈列,而在于被需要的人发现。
书店也是我自己的课堂。午休时分,当阳光洒在文学区的橡木地板上,我会带着笔记本坐在窗边。从《如何阅读一本书》中,我学会了“解剖式阅读”;在《深阅读》的指引下,我尝试建立自己的“知识图谱”。但最珍贵的课程来自一位常客,退休的语文老师王先生,他总说:“读书不是往脑子里灌水,而是点燃火把。”他教我边读边在书页边缘写“对话”,把每本书都变成一场跨越时空的交谈。
这种阅读方式彻底改变了我。以前读书总想一口吞下整片海洋,现在学会了在某个段落驻足,任思绪随着文字的溪流漂向远方。当我在书店的读书会上分享《瓦尔登湖》时,不再复述梭罗说了什么,而是讲述这本书如何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消费习惯——就像梭罗说的:“我们被迫生活的如此认真,这是何等的奢侈。”
现在随着数字化改造。作为书店的职工都要熟练地操作智能查询系统,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慌——我会不会被时代淘汰?某一天我翻开加缪的《西西弗神话》,读到“攀登山顶的拼搏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时,泪水突然涌出。第二天,我就联系了别的旗县的同事学习系统内容。现在,我不仅能帮老读者找到他们记忆中的那本书,还能为年轻人推荐电子书资源。书教会我的,正是这种永不止息的成长。
最近经过门店时,我偶然发现了一本《傅雷家书》。翻开扉页,傅雷写给傅聪的话:“人的一生,总是在高潮和低潮中沉浮,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我将这本书放在收银台旁的展示架上,第二天就被一位白发老者买走了。看着他颤抖的手指摩挲着封面的样子,我知道这又是一次命中注定的相遇。
站在书店的玻璃门前,看着夕阳将书架染成金色,我突然理解了博尔赫斯说的“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在这个电子阅读盛行的时代,纸质书店或许终将式微,但书籍给予人的光亮永远不会熄灭。六年来,我见证了无数人与书的相遇:备考的学生在教辅书架前蹙眉,年轻的母亲为孩子挑选第一本图画书,老者在古籍区寻找青春时代的记忆……而我自己,也从那个在书架间迷路的小女孩,成长为能够为他人指引书海航向的人。
当最后一抹阳光从《安娜·卡列尼娜》的封面移开时,我轻轻将书推回原位。明天,它或许就会与某个需要的读者相遇,就像当年的我与《城南旧事》,就像那个高中生与《被讨厌的勇气》。在这个充满可能性的空间里,每一本书都在等待它的读者,每一个故事都在寻找继续书写的笔。而我,何其有幸,能够成为这些相遇的见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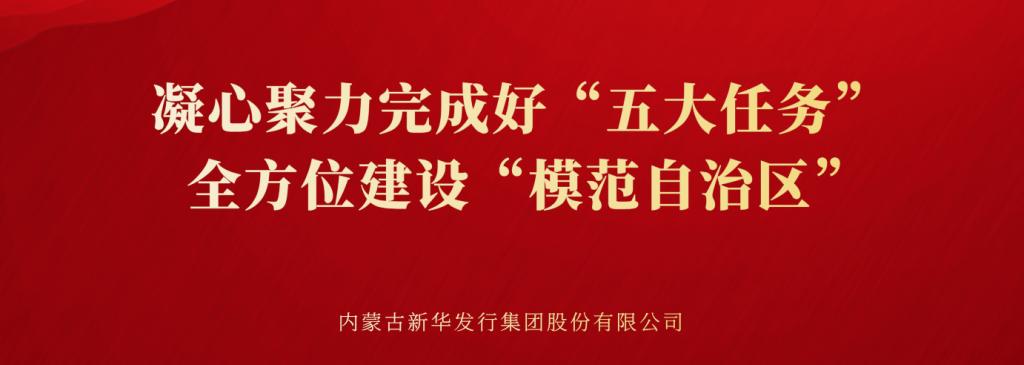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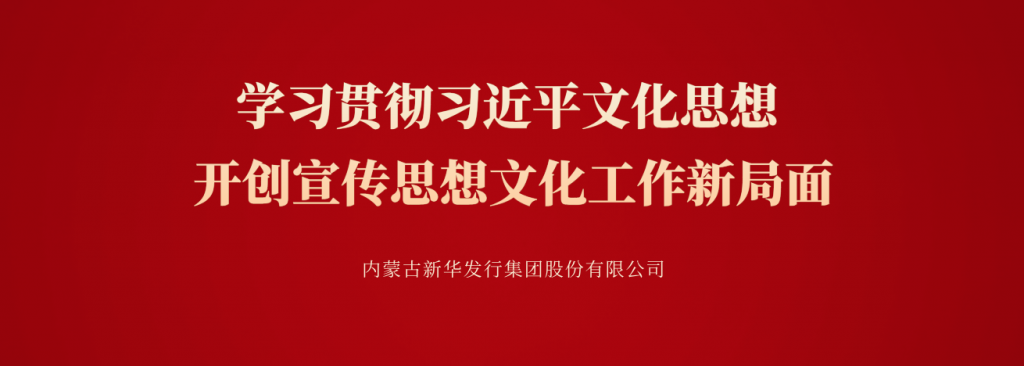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 15010202150364号
蒙公网安备 150102021503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