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上班,推开书店的玻璃门,那股熟悉的油墨混着旧纸张的味道就涌上来。换上洗得有点发白的围裙,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日子久了,闭着眼睛都知道《百年孤独》挨着《围城》,《平凡的世界》上层是《活着》。书脊上的名字天天见,像街坊邻居一样熟,但也没太往心里去——它们立在那里,我负责让它们站得整齐,码得顺溜,仅此而已。
这活儿干了小半年后,说实话,有点闷。直到那个有点慌神的小伙子闯进来。他满头大汗,在书架前打转,眼神像迷了路的鸟,手指头在一排书脊上划拉半天,就是下不去手。我凑过去:“找啥书?需要我帮你找吗?”他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老师,要评职称,急用!领导让找本讲‘内在力量’的书!”我脑子里飞快转着那些“街坊邻居”的脸,灵光一闪,想起前阵子理货时翻过几页的《活出生命的意义》,集中营里熬出来的心理学,讲的不就是人心里的那股劲儿?我立刻蹲下身,手指精准地划过第三层书架靠右的位置,抽出来递给他:“看看这本,维克多·弗兰克尔的,讲人在绝境里怎么找到活下去的意义,算不算‘内在力量’?”伙子一把接过,眼睛扫过封面,那紧锁的眉头“唰”地展开了,连声说:“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太谢谢您了!”他抱着书冲向收银台的背影,像卸下了千斤重担。我站在书架间,手里仿佛还留着那本书粗糙封面的触感,心里头一次觉得,这围裙穿着,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原来这些站得笔直的书,真能解人的急,暖人的心。
打那以后,书架在我眼里活过来了。整理时不再只是机械地掸灰、对齐,手指拂过那些或新或旧的书脊,会下意识地想想它们各自藏着什么宝贝。碰到顾客询问,也不再简单指个方向。一位常来翻看历史书的大爷,有天突然问我:有没有讲‘普通人怎么过难关’的书?我立刻想起《布鲁克林有棵树》,那棵水泥地里顽强生长的臭椿树,不就是普通人的韧劲儿?另一位妈妈,为沉迷游戏的儿子发愁,眉头拧成了疙瘩。我犹豫了一下,没推那些教育理论大部头,反而抽出一本薄薄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递过去:“要不让孩子试试这个?一个找宝藏的故事,挺薄,说不定能看进去。”过了一阵子,这位妈妈笑着跟我说,儿子居然把书看完了。她说这话时,眼里的愁云散了大半。这些小小的回应,像细碎的火星子,噼里啪啦地溅在我心里,把那份日复一日的单调工作,慢慢烘烤出一点暖意和光亮。
弗兰克尔在书里写:“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自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 这话像颗种子,落在我这方寸之地的书堆里,悄悄生了根。我每天依旧穿着围裙,穿梭在熟悉的书架间,重复着理货、上架、导购的动作。但心里头明白,自己不再仅仅是个“搬书的”。我更像一个看林人,守着一片能滋养心灵的树林。哪本书里藏着坚韧的种子,哪本书能点燃希望的火苗,哪本书能解开一个心结……我渐渐摸到一点门道。每一次把合适的书送到需要它的人手里,就像点亮了一盏小小的灯。这灯光或许微弱,却实实在在地能穿透一些迷茫和困顿。
下班时间到,我脱下围裙,锁好大门。走出书店,城市的喧嚣扑面而来。回望身后,书店的招牌沉默而笃定地“站”在那里。我知道,明天我还会准时推开这扇门,穿上那件围裙,继续在这片书海里摸索、传递。因为这份看似普通的工作,让我真真切切地触摸到了,那一本本沉默的书页里,蕴藏着的、能点亮人心的微光。这光,不仅照亮了找书人的路,也稳稳地照亮了我自己脚下这片平凡却踏实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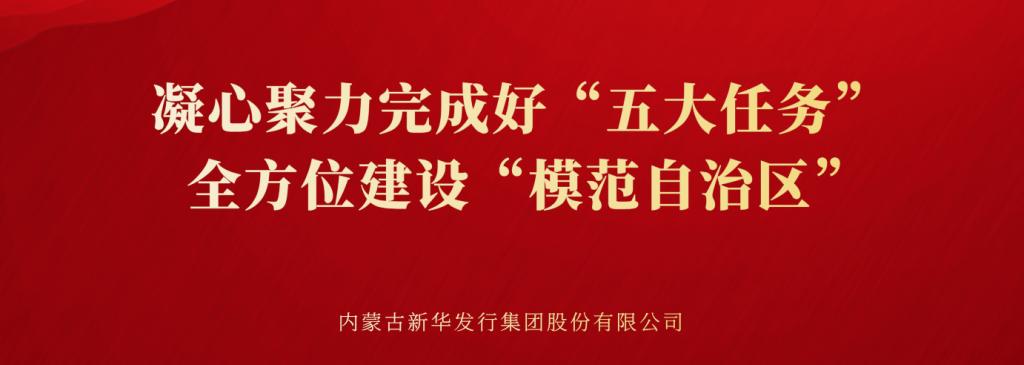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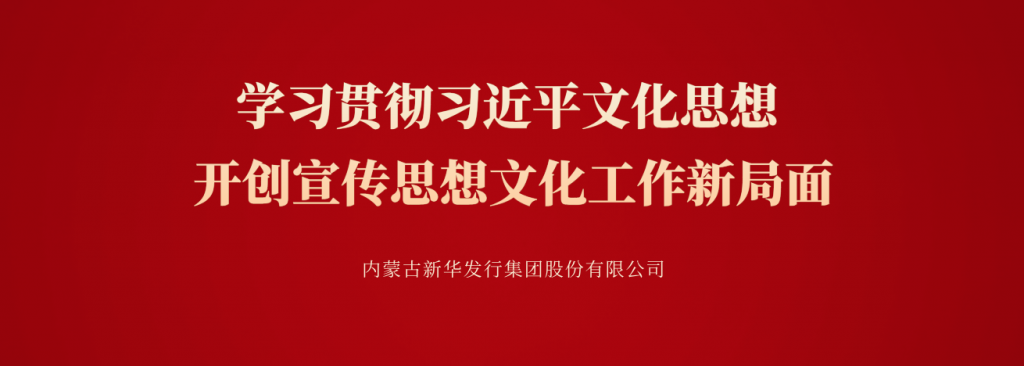


 蒙公网安备 15010202150364号
蒙公网安备 15010202150364号